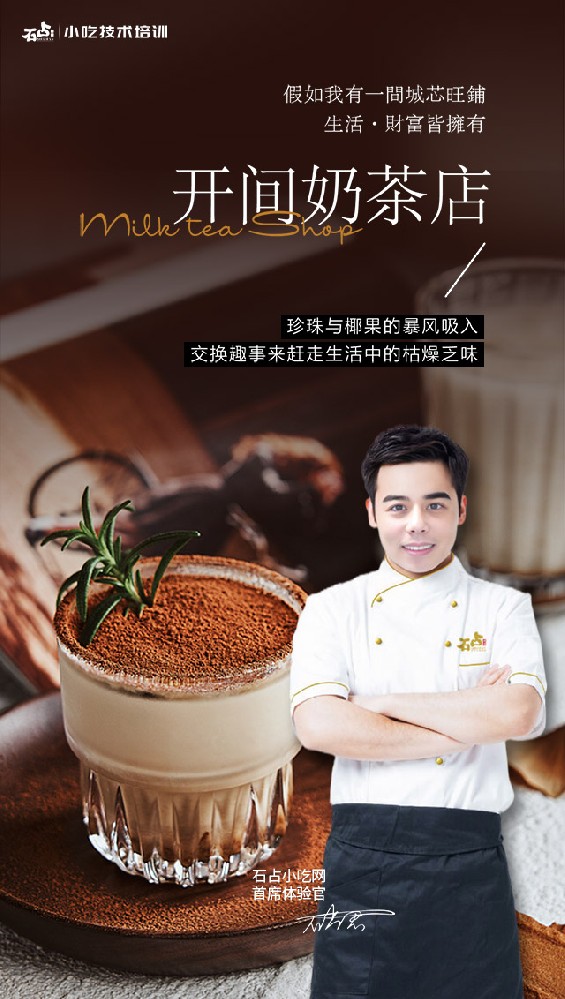
一家北京很地道的安徽淮南牛肉汤店,关张了。
营业的最后一晚,没有出现戏剧性的老客满盈,人稀稀拉拉,老板也得闲,站在门口连抽好几根烟,看我一口葱油饼一口千张吃得欢,对我投来感谢的微笑。当晚食客里有位饿了么送餐员,听他们聊天像是认识了好几年。我只见过这个送餐员一次:那天北京很热,他食欲仍旧旺盛,一个人吃完了一碗牛肉汤和六块葱油饼。
从他们言语之中,我得知自己误打误撞上店里最后一锅牛肉汤。送餐员问老板之后的打算,老板说,还是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店铺。送餐员慨叹在北京谋生的难,老板也应和,转脸自嘲般跟妻子说起俩人刚来北京时的憧憬:要把淮南牛肉汤做成像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那样,每条街上都能有一家的连锁。
没想到几年不到,连锁梦变成生存梦,北京做类似安徽小吃的馆子也肉眼可见的减少。前阵子石家庄爆出新闻,当地著名安徽牛肉板面,将正式去除“安徽太和”原籍,改名为石家庄牛肉板面;另一个南京朋友也曾跟我吐槽:外地人到南京都要“喝馄饨”,但其实做馄饨的绝大多数都是安徽安庆,南京自己的柴火馄饨早没了,但对外说起来,都是南京馄饨。
她可能忘了我就是安徽人,言语之间没避讳。不过转念想想,大多从安徽走出来的小吃,也无非这两个命运:要么跟淮南牛肉汤一样,怎么都扩张不起来;要么被其他省同化,安徽人的痕迹名字被隐匿消失。
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,安徽人不少,但安徽小吃是失语的。
即便常吃石家庄安徽板面的人,也少有知道安徽北部阜阳市太和县,这个板面出生地。这里距离河北石家庄 678 公里,当年阜阳人沿着铁路北上,留在了石家庄奋斗建设。板面也一起跟着走了出来,在石家庄落地,在石家庄生根发芽。
最初板面其实是羊肉汤底,但石家庄本地吃不惯山羊的腥膻,被换成了接受度更高的牛肉汤。加量的辣椒和盐,也是来石家庄后的特色。安徽籍老板们善于自我革新,却也因此遭受非议。争着争着,板面的名号倒是被大家熟悉了起来,成了安徽小吃在外省的头号招牌。
后面大家就知道了。石家庄开了发布会,将安徽板面正式改名为石家庄板面,“去安徽”化成了板上钉钉的新现实。
反观同一时期外出闯荡的淮南牛肉汤,就缺了些运气。
我成长于皖南一带,但淮南牛肉汤在我人生前二十年的饮食轨迹里,也是缺失的。淮河和长江从安徽横贯穿过,把这里“撕裂”成了皖北、皖南、皖中,三个语言和饮食习惯都不同的地区。所以我们会自嘲说安徽看起来像三个省,饮食语言各不重合,唯一能团结起我们的,大概就是共享阴冷的冬季。
皖南虽”南“,冬天早晨却处处弥漫透心的冷,一碗滚烫的淮南牛肉汤最是暖身:牛油味厚重的汤底,滋润着同样柔韧的千张和粉丝。刚出炉的葱油烧饼烫得没法儿直接上手拿,但葱油饼表面稀疏撒落的芝麻和烤得干瘪焦黄的葱花,又配合着赤裸裸的荤油香味叫人等不及想吃它。
于是第一次接触后,我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。
牛肉汤的烹制不甚繁琐:黄牛肉、牛骨头置于锅内,卤料是每家店的秘密,一道放进锅里,炆炖几个小时,直到牛肉松烂,汤味饱满。这个步骤没什么捷径,就是要舍得花时间,让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分释放。所以卖淮南牛肉汤的小店,通常都在后半夜熬制汤底,偌大的铁锅,咕嘟翻腾到天亮,香味从厨房溢到前厅,以示汤底大功告成。
切成跟银丝面的千张,连同几片牛肉、一把粉丝一起放进笊篱,在腾着热气的大锅里上下几个翻滚,很快就能熟。锅面上飘着的辣油已经跟牛油的味道浑然一体,所以即便你点的是不辣的牛肉汤,喝起来也还是有隐隐的辣意,有点刺激,但不生猛,一碗下肚,鼻头不知不觉就蒙了一层细汗。
这种出身市井的小吃,有种与生俱来的坦荡,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揣度厨师的想法和食材组合的奥义,酥也好,香也罢,全都开诚布公,吃起来有种难得的放松。所以辨识淮南牛肉汤的方法之一,就是开放式的厨房,和一口永远都在炖牛肉牛骨的宽口大铁锅。
之所以说缺失运气,是因为淮南牛肉汤也经历过与太和板面类似,不断动荡和自我革新。
淮南,顾名思义正是淮河以南,虽说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虽说踏入淮南就算进入了南方,但地处南北分界线上的淮南,难免还是有了很多南北混杂融合的饮食。牛肉汤就是典型的一例,早期汉族人不能私自宰杀耕牛,淮南汉族人聚居地没有吃牛肉的习惯。北方游牧民族将吃牛羊肉汤的习俗带到了淮南,有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淮南牛肉汤。最开始在淮南出现的牛肉汤,大多都保留着北方回民饮食的简单质朴,一碗牛肉汤货真价实,里面只有牛肉和汤。
大概是后来,淮南人觉得这牛肉汤缺了点自己熟悉的滋味,于是加入江淮一带的人爱吃的千张——这种将豆腐压扁后,制作出的一种又薄又软,吹弹可破的薄豆皮,让这碗迁徙过来的牛肉汤多了几分细腻和柔情。粉丝、豆饼也渐渐加入了淮南牛肉汤的阵营,彻底将这碗北方大汉改造成了本地刚柔并济的书生。
走出淮南,则是因为淮南盛产煤矿工人。淮南曾是产煤大区,煤矿工人数量众多,最先富裕起来的煤矿工人喝得起牛肉汤,也习惯了每天一碗暖呼呼热腾腾,口感丰富的热汤下肚。随着运煤所搭建四通八达的铁路网,他们跟随煤矿奔赴远方,也带着淮南牛肉汤去到了四面八方。
但碗走出淮南的牛肉汤,已经被调教成颇有自我风格的模样,想坚持住自己千张粉丝和浓厚牛油辣子的搭配,创造属于淮南自己的容貌。因此,造就了和太和板面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偌大的北京城,满族和蒙族的羊汤羊蝎子涮羊肉率先笼络了人心,一碗从淮河以南过来的汉族牛肉汤,俨然像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外邦人,被排挤在围墙之外。再往沿海南方,四季潮湿闷热,吃完背后透一身汗的牛肉汤,本就不符合当地饮食习惯,再加上飘着一层让广东人望而退却的红油。这碗原本融合了南北习俗的汤,却变得在南北都不讨好。
出走半生的安徽淮南牛肉汤,真正带有安徽个性的滋味,在出省的路上节节告退。
大城市的餐饮,总归是要看大众脸色行事的。淮南牛肉汤原本以为自己兼具南北基因,能大杀四方,但绕了一圈才发现,只有安徽自己人才能吃懂。
这也多少呼应了安徽如今的尴尬:南北方交界不供暖,江浙沪周边不包邮。虽然地处内陆腹地,还有点不南不北,不中不东,曾努力地把不同地方人的喜好都融入一碗牛肉汤中,但偏偏这种近乎混杂的内敛和包容,只剩下安徽人自己懂。
当和外省的朋友聊起,被提到说安徽好像没什么好吃的,总觉得欲辩已无言。符离集烧鸡、合肥鸭油烧饼、寿县大救驾这些名字放在全国饮食版图里的确是生疏,在外的安徽人似乎也不爱争个老家饮食的长短。他们总是笑笑,然后继续勤勤恳恳地第二天凌晨四点摸黑起床,支起小摊,揉面发面,撑起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早餐铺。尽管偶尔网上也会有段子为安徽正名:如果你想画出一张雄鸡图,那么你打开地图App,将全国的安徽包子铺用线条勾勒出来就行。
我在北京所熟悉的那家淮南牛肉汤,关张那晚已经接近立秋,晚上的风夹带着些许凉意,喝完汤,我跑去找老板结账,跟他说好难过,今后不知道去哪里还能喝到这么淮南味道的牛肉汤。老板先是低了下头,然后似乎无奈,有似乎自言自语的反向宽慰我:北京这么多卖牛肉汤的,要喝好的还是有的。
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留在北京。我只是知道从明天开始,我的生活里会少一碗淮南牛肉汤的滋味。并且,偌大的北京城,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另外一家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