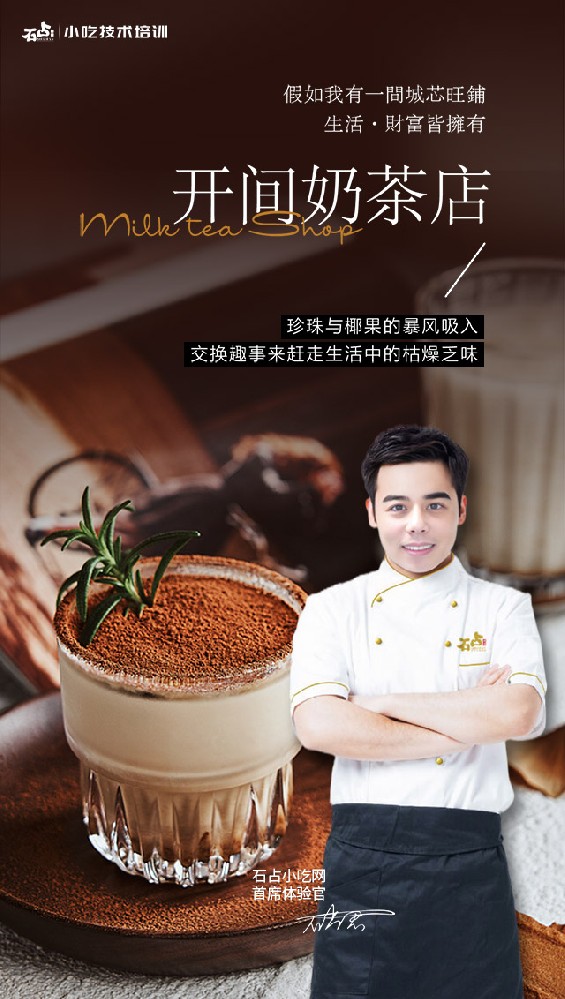
我家冰箱里永远会有个位置留给浆水。
毫无悬念 ,我是个甘肃天水人,自带浆水基因的天水人。
算不上百年传承,但我家浆水可上溯最久远的开端,是1959 年。
那一年我的姥姥17岁,站在厨房里跟她的大嫂学习腌浆水。嫁到姥爷家之前,姥姥没进过厨房。跟同村的其他女孩相比,她算幸运的,读书一直读到了高二才嫁人。从学生到主妇,姥姥的转变从第一缸浆水开始。
迎接姥姥的,是从地里掰下正在等待清洗的一背篓白菜。清洗过后,这些白菜将会被天水人转化成一种迂回悠扬的风味—浆水。
在小农经济作为主导的漫长时间,浆水是天水人一日三餐离不得的东西。好做,便宜,且能保留蔬菜的鲜香清爽,给单调的饮食增加滋味。
村里人都说,姥姥聪慧。她很快就掌握了做浆水的技能。跟大多数甘肃妇女要做的其他家事一样,腌浆水并不难,但琐碎、需要忍受重复的耐心。
那个时代,每个天水人家里都至少有一个腌浆水的缸。姥爷家是大家口,缸也大,一米多高的缸就有三四个,人可以很从容地站进去。姥姥每天跟大嫂、三妹一起下地干活,带回腌浆水的蔬菜。浆水的配料没有严格的秘方,卷心菜、苜蓿、苦蓿、蒲公英、芹菜……什么菜多就用什么。有时缸大菜多,切好的菜需要分三四次进锅焯,分批次投进缸里,是个考验身体的体力活。
那是旧式近三十平米的大厨房,很多的锅和柴火,很大的灶台和浆水缸。一年又一年,厨房的大缸迎来送走了一批一批的蔬菜,姥姥却始终站在大缸旁,重复相同的动作:洗菜、切菜、焯水、投缸、和面、擀面、舀浆水、做饭……她的孩子一个个出生,在这个厨房里哭泣、入睡、嬉戏、争吵,慢慢长大。
童年的记忆是有浆水酸味的,但孩子并不排斥。孩子总是在厨房追着姥姥,但姥姥要做的事越来越多,白天下地、做饭、喂猪喂鸡,晚上给妈妈和舅舅做鞋做衣服……甘肃土地贫瘠,白面(小麦面)不易得,大多时候一日三餐就是苞谷面。农忙的时候,姥姥需要在中午孩子们放学前赶回家做饭,再回地里干活。经常就是苞谷面搅一锅搅团,再炝一锅浆水。
现在,浆水搅团算是一个很可以代表天水风味的小吃,会被摆在精致的酒店餐桌上招待客人。但在当时,那是一种能勾起很多委屈的食物。妈妈到现在还会跟我说,有时候中午放学,姥姥已经下地了,一个人进厨房看到那锅已经变凉的搅团和浆水,会很想哭。
生养了四个孩子的姥姥在那片田地上耕种了30多年,经历了文革和包产到户,在儿女成家之后照顾了十几年太奶奶……要承担的委屈,可能不止是每天都要吃同样的浆水搅团。有时我会想象,她每次把菜投到浆水缸里的时候,都怀着怎样的心情。小时候,我会听她讲她对厨房的厌倦,当然听不太懂。其他时候,我不知道姥姥会跟谁说,也许都化到了浆水清白纯澈的液体里。浆水的酸虽然柔和,但也有股很有辨识度的劲在里面,很像姥姥。
农忙过后,姥姥会想尽办法用手头的粮食做出变化的滋味,浆水的形态也丰富起来:浆水面,苞谷面根根,酸菜馍,面鱼,馓饭……六月中旬,新打的麦子磨成了面粉,吃一顿浆水面是必不可少的庆祝仪式。一家人在廊檐下摆好桌子,炒菜斟酒,等姥姥的面出锅。
“端饭了!”话音还没落,孩子们已经在厨房门口排好了队。中午日头大,廊檐底下却有凉凉的风,清爽的浆水让面香更为突出,大人们互相说着:“今年的面真劲道。”孩子们一声不吭,闷着头只顾吃。那是踏实、饱足的一餐,每一年,姥姥用这样的仪式加固自己对土地的信念。土地公平且诚实,会用饱满的麦粒回馈每日的劳作,像此时此刻围在身边的,这些长得飞快的孩子。
冬天第一场雪,一家人照例要吃顿热乎乎的馓饭。灶上架起火,大锅里的水烧开,玉米面细细撒入,边撒边搅,慢火熬煮。越来越浓的玉米面在柴火的挑拨下,突突突地往上冒泡,又很快钻下去,结成果冻一样的半凝固状态。厨房里散发着热气,一盘一盘的菜被端出去:土豆丝,胡萝卜丝,炒辣椒,包菜,热油辣子,炝浆水……三代人坐在热得烫屁股的炕上,围着一张小方桌,手里端着盛着馓饭的碗。红红绿绿的菜一样样码到光滑如鸡蛋羹一样的撒饭上,外面雪花纷飞,除了一起吃完这锅饭,再没什么要紧的事。
四个孩子里,妈妈是唯一的女孩,姥姥不让她下地干活,想把她的手护得白白净净的,想让她好好读书。小学升初中,成绩一直很好的妈妈没上榜,姥姥去找镇上的中学老师,想让妈妈读初中,老师没答应。后来妈妈的班主任联系到姥姥,说漏写了妈妈的名字,姥姥理直气壮:“我晓滴嗷的娃能考上,学习一直好着哩木!”踏实了。
妈妈一直想去城里工作。姥爷就在城里工作,有时带同事来家里。他们穿得时髦、说话的腔调也洋气,跟村里的人不一样。妈妈羡慕他们,想跟他们一样,能在城里挣钱,买自己喜欢的喇叭裤。18岁,妈妈高中毕业,去参加城镇招工考试,到了市里工作。
妈妈一个人住单位宿舍,宿舍离城区很远,周六日食堂不做饭,周围很难买到吃的。第一个月发了工资,她十几块钱买了个煤油炉子,添置了厨具。第一顿饭,妈妈从食堂的师傅那里要了一碗浆水,回家搅了白面疙瘩,做了浆水拌汤(类似于疙瘩汤)。很简单的一餐饭,但滋味是新的。那是一个农村女孩进入更广阔天地的成就感,朴素,充满希望。
妈妈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,有了我。
作为一个优秀的事业女性(彩虹屁),妈妈结婚之后很少自己腌浆水。记忆里都是让我从外面提回来。偶尔来了兴致也会自己做。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,有天周末的午后,妈妈提了一大袋芹菜回来,宣布她要腌浆水。我跟在她后面,干点没有技术含量的活,听她很兴奋地跟我介绍腌浆水的步骤。厨房里,芹菜脆生生的绿,水汽氤氲,跟邻居要来的浆水引子卧在碗里,让人忍不住想喝一口。
忙活了好一会,到了投缸的环节,妈妈发现自己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——我们家没有浆水缸!最后只好拿一只搪瓷盆来顶事。腌完浆水之后,妈妈就像一个第一次养蚕宝宝的好奇小朋友,隔一会就要去浆水盆那里看一下,嘴巴里念念叨叨。
过了两三天,浆水腌好了,老实说,不如外面提来的好——酸度不够,因为一些环节没有把控到位进了水,还容易起霉花。在我非常诚实地做出了自己的反馈之后,妈妈面不改色,总结了一些类似于“需要一个正经的缸”“要小心不能进水”的经验教训,仍然充满感情地把浆水舀出来做拌汤。几天之后,霉花的发展超出了妈妈的预期,我们家又悄然无声地回到了从外面买浆水的传统。
但妈妈做的浆水面却是极好的,即使是在家乡,我也很难在别家吃到像我们家那么完美的浆水面。说起来,浆水面的做法实在是很简单,不过是面条煮好,浇上用蒜瓣、干辣椒炝锅的浆水,夹两筷子炒好的韭菜,调小勺盐和辣椒油。
但我后来离开家自己煮才发现,简单的食物,做好却是需要很多功力的。浆水面对面条的要求很高,不是像兰州牛肉面那样有明显的脾气,但也绝不能绵软。需要在手和刀的力道、擀面杖的粗细、面粉和水的比例、煮面的时间中拿捏精微的度,错一点都会破坏面的口感。但妈妈对这些从来都谙熟于心,从容不迫。一碗完美的浆水面,面条应该是不沾不连、根根分明、带着不显山露水的筋骨,那种口感,只有妈妈做得出。
炝浆水也是,很奇怪,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热油炝锅的动作,不同人操作却有全然不同的滋味,完全无法复刻。只有妈妈炝的浆水,能恰恰好地逼出干辣椒的焦香、熟蒜瓣的醇厚,让浆水酸香之外又很有层次感。配菜和辣椒也有讲究——韭菜必须要挑农家小摊那种五寸长的新韭,辣椒油则是姥姥自己种的辣椒,手工磨成粉,热油炝好,不辣、很香。再配上橙红碧绿的胡萝卜丝、炒南瓜秧,能让人吃得魂不守舍。
理所当然地,那碗浆水面成了我的乡愁。说起来,浆水从前是经常被我们小孩子调侃的食物,一部分是因为它跟从前的匮乏年月有太紧密的联系,一直不算是什么“高级”的食物,甚至有“年初一不吃浆水”这样的说法;一部分也是因为,那种发酵酸就像老北京的豆汁儿,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。但现在,躺在北京的出租屋里,想起家的时候,舌尖泛起的,往往就是这种很难形容的酸。
这好像是离开家的人才会有的体验:某个你过去从没稀罕过、甚至有点嫌弃的食物,因为不再能够随时吃到,突然就成了一种固执的念想。恍然间才发现,那个东西早已渗进味觉记忆的最深处。
有个从高中就认识的老友,在北京待了快10年,去年夏天的某天,心情燥热,突然想浆水想得不行,专门跑去菊儿胡同吃了碗浆水面,一下子就熨帖了。过了好久还跟我感叹:“在家的时候,其实一直都不爱吃浆水,现在却成了乡愁。”
这种味道渗入的程度是如此之深,以至于吃顿浆水已经成了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“天水娃”每年回家的固定项目。过年回家,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们聚会,见面打招呼都是:“吃浆水面没?”有个朋友要在晚饭时候提前离席,给了个不能不接受的理由:“我妈喊我吃浆水面啦!”
今年年初三,跟一个远嫁云南的朋友见面,她刚在妈妈的“威逼利诱”下吃完一大碗浆水面。其实明明是要一起出来吃饭的,但妈妈说:“不吃?你是不是嫌弃我们这的东西了?”这是西北女人表达关爱的方式,泼辣、不容分说里藏着感情。朋友一边抱怨,一边乖乖地吃完了那碗面,好像也做出了一份保证。妈妈心满意足端走碗:“好了。你现在想干啥我都不管了。”
想吃浆水的时候,我会想到姥姥。这几年,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,姥姥不愿意到城里跟妈妈舅舅一起住,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那个她17岁来就一直没离开的小村庄。大缸变成了小缸,浆水还在陪伴着姥姥。妈妈还是更习惯买浆水,每次回家,下高铁的那个晚上,妈妈会做浆水面,配最鲜嫩的时令菜迎接我。我在北京,平均一周做一次饭,冰箱里经常很空荡,不过最近,朋友寄来了一大箱浆水,够吃一阵子的了。
前几天看《十三邀》,听晓卿老师说起这几十年我们吃饭场景的变迁,一大家人围在一起吃饭,是外国人对中国饮食的典型印象,却是今天的我们正在慢慢失去的。从一个大家族的厨房,到三口之家,再到公寓楼里的一人食,浆水似乎也是一个见证者。各家的浆水都有自己的味道,它们浸润着天水女人的性格和智慧,也见证着不同但相似的故事。关于如何坚实具体地生活,如何把单调转化为美味,如何在硬生生的话语里传递温柔……
一代代的女人,从厨房走到更广阔的天地,吃潮汕菜北京菜云南菜贵州菜西餐,已经不必跟那只浆水坛子绑在一起,但仍然会在某刻,对那种清淡倔强的酸念念不忘。
